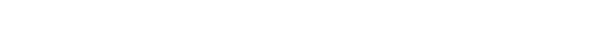今天,何光荣老师主讲其专著《中国古代教育哲学》(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)。作为第一讲,何老带领大家思考《中国古代教育哲学》一书的前两章:本体论和人性论。其中,重点是儒家的本体论和人性论。初次听何老讲授,理解起来有些吃力,下面是一些粗浅的感想。
本体论研究“世界的本原或本性的部分”,暗含着探究现象背后的物事的意向。这里的重点是,在现象背后,设想有更值得关注的东西——比起现象来,背后的东西可能恒常不变,具有更高的真实性,且决定着现象的变化。而哲学,在古希腊思想的起源处,就包含着探究恒常不变的东西。我们今天的自然科学,很大程度上联系着古希腊的自然哲学观。
在中国古代思想文献中,《易经》包含着探究天道的内容。这样表述,想说明《易经》原始的占卜特征。那么,天道(自然)和占卜之间是什么关系呢?推测是,先人观自然物象拟设八卦,复用六十四卦模拟更多的物象和生成变化关系,从而做出预测。因此,占卜(预测)建立在对自然物象的观察、模拟和遵从上。《易》学在历史上分为象数和义理两派,前者恰是一种物象比推和演变,后者则是对自然、天道和人事的说明。
宋朝时,诸儒皆从《易》阐发世界的形态和构造,进而论说性理。这一现象一方面源于对佛教宇宙观的响应,要从万物存在的层面论说儒家理念;另一方面也源于《易》在六艺中具有独特的内容,包含着对自然万物的描述和义理建构。例如,从天引出“健”,从地引出“坤”,从阴阳变化引出人在各种情况下的进退和吉凶。“体用一源,显微无间”,何老认为“即存在与现象之统一也”。从这一点来说,中国思想注重统一,而非偏重于现象背后的某种本质”。
“一阴一阳之谓道,继之者善也,成之者性也。”于此,何老引出作为本体的“善”。“自诚明,谓之性,自明诚,谓之教。”“不诚无物。”从《中庸》中,何老得出“诚”的三个意义:“一是表现哲学和自然科学中之实在也;二是表现人生哲学之诚实也;三是表现教育哲学之渊源也。”在阐释“教”的作用时,何老认为:“教非人类之目的也,乃是启发人之自我认识能力,激励人之自我完善志趣,谋求人类理想之推进和实现也。”这一点,很有启发意义。
关于人性问题,何老在性善论的基础上,认为离开人性之善,就谈不上“教”和“政”。(第70页)善性不仅仅是指人性,也指物性。“善”是一种精神,“推动着宇宙的变化和万物的起源。”同时,把孔子看作性善论的先驱,认为“穷理尽性”的对象就是善的精神。孟子继承孔子,为性善论奠定了基础,被朱熹称赞说“有大功于世”。不过,欧阳修认为“圣人之教人,性非所先”。(见《四书章句集注》之《孟子序说》)这里,引出两个问题:一是人性究竟是善还是恶,二是教育要先教什么。
如果我们可以找到一个东西,用这个东西来衡量人性的善与恶,那么问题就迎刃而解。从告子和孟子就人性善恶发生争论以来,之所以聚讼不决,恰是缺乏这样一种衡量。即使孟子在书中做了辩解,却仍然无法让所有人信服。例如:荀子就提出了人性为恶,善事乃是人们有意为之导致的观点。固然,我们可以从信服人性善更有利于教育人心、敦化风俗、施行仁政的角度来选择信服人性善,可是这却无法让那些不从以上角度考虑的人选择信服人性善。类似,我们可以因信仰人性善能导致生活更安乐这一点来相信人性善,却无法让看不到这种关系的人来信服人性善。在这种情况下,我们如果把教育和淑世的途径完全建立在“人性善”上,就需要特别谨慎。这里要说明的是,因为相信人性恶而采取严刑峻法,更不可取,尤要防范。但是,基于人性为恶倾向的警惕,进而更加注意在制度设定上的低道德预设,却需要参考。在国家治理层面,更是如此。
无论人性是善还是恶,我们都要教育人们向善。只是如果善为人性,我们只要反求自身即可。如果不是,则需要某种注入、教化或强有力的培育。这里,联系上面欧阳修的观点,可能要特别注意人的无知和学习、教育。此外,在自然科学日趋客观化的今天,从天道、天理、自然万物上引申出仁义道德,更属不易。何老认为,“性善论与性恶论二者非发自对立之两极之端也,乃是同一源流走向之论也”。前者为源,后者为流,别具创见,引人发省。